都市快报讯 据香港有线新闻报道,香港作家西西今晨因心脏衰竭于医院安详离世,享年85岁。
香港素叶工作坊讣告发文,“西西一生,精彩、愉快,并且有益,有意义。我们都会怀念她。”
素叶工作坊前身是素叶出版社,由西西与友人一手创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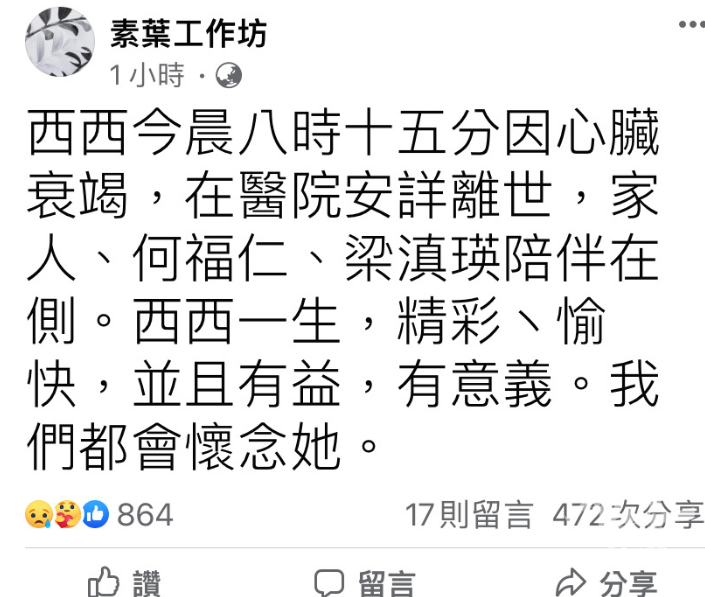
学者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中午也发微博称:“香港著名作家西西(1938一2022)今晨在港逝世。她留下的小说、散文、童话等是20世纪中文文学中的瑰宝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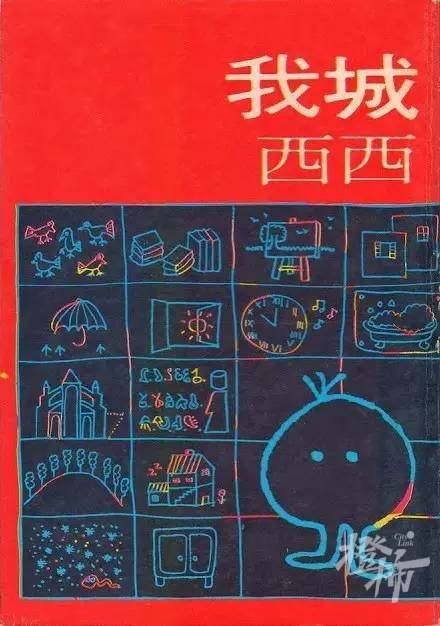
《我城》素叶初版
西西本名张彦,是当代知名香港作家,1937年在上海出生,上世纪50年代移居香港。
她于1974、75年写了一个关于“我”的香港故事《我城》,在报纸杂志连载,后来结集成为同名小说,在香港及台湾都曾获奖。
代表作还包括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《店铺》《碗》《飞毡》等,其中多篇作品成为中学中文科教材,小说《哀悼乳房》亦在2006年被改编拍成电影《天生一对》。

说起香港女作家,被大众所熟知的似乎多是张小娴或者亦舒,其实,读香港文学,西西是最绕不开的。
毫不夸张地说:她是香港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之一。香港众多作家中,西西无疑是最具生产能力的。
曾有人问梁文道:“香港有文学吗?”
梁文道说:“有,西西。”他认为西西是最能代表香港的作家,是作家中的作家。
王安忆曾评价她西西是“香港的说梦人”;余华说她是极具独创的作家;王德威说,因为她,文学足以成为香港的骄傲。
西西1979年出版的《我城》,早已成为香港的象征。
她的作品,如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《我城》《哨鹿》《我的乔治亚》,几乎代表了一代香港文学的最高水准,被收入各大教材,成为民众的“文学通识课”。
早在2006年,豆瓣便建立了关于她的小组,在她的作品还未被大规模引进时,很多人已经成她的死忠读者。他们花高价,一本一本买来西西港版、台版的小说,如饥似渴,只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她的新作。
那段“收书”经历,成为西西粉丝们的共同美好记忆。

在香港文学中,西西是个美丽的异数,她的写作超出了香港为她划定的界域,她的才情和智识,给一代读者带来了文学的启蒙。
1979年和1980年,她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和《素叶文学》杂志,成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主要阵地。
1978年的素叶出版社和1980年的《素叶文学》,是香港文学的高峰。它既出版了多种香港文学经典作品,如西西的《我城》《哨鹿》《春望》、也斯的《剪纸》、马博良的《焚琴的浪子》、吴煦斌的小说集《牛》、戴天的《渡渡这种鸟》、古苍梧的诗集《铜莲》、钟玲玲的《我的灿烂》、何福仁的诗集《龙的访问》、淮远的散文集《鹦鹉千秋》、康夫的诗集《基督的颂歌》等,也出版了多种文学评论作品,如郑树森的《奥菲尔斯的变奏》《艺文缀语》、董桥的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中和胡须外》、何福仁与西西的对话集《时间的话题》等。
《素叶文学》除发表作品外,也刊登香港文学评论。

西西早年作品大多在台湾出版。她笔下的“我城”,既是香港人最熟悉的日常,又是香港人有点陌生的幽默,温和,甚至童趣的存在。
80年代初期,西西的走红是在台湾。她那篇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,曾在台湾刮起旋风,文艺青年们纷纷模仿小说中的句式,说话或者写作。“像我这样的一个公务员”、“像我这样的一个母亲”层出不穷。至今,台湾的书店仍将把西西的作品当做神级供奉。
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讲述了一个殡仪职业的女化妆师的爱情故事,这个故事有真实原型。
西西的父亲去世那年,她在殡仪馆碰见一个远房姑姐,叫吴金枝。这位姑姐是一个殡仪化妆师,西西父亲的仪容便是她完成的。
多年来,姑姐都没有结婚,因为男人听到她的职业就退却了。由于化妆技术好,她也会收徒弟,她收徒弟时会先问人家,做这个会不会怕的?将来没有男人敢娶你,你也可以吗?等得到肯定的答复,她才会同意教人家。
这篇轻松又沉重的小说,所要探讨和表达的,不仅仅关于爱的承诺是否会改变,女性的边缘化地位,还有社会如何看待异质,社会对异质的接受度到底有多大的问题。西西早期的作品,小说的切口都很小,表达的内涵却深刻沉重。
短篇小说集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中,有一则名为《感冒》的小说,讲的是一个女人找回自我的故事。
这个女人即将走进婚姻殿堂,但她并不爱自己的未婚夫。快结婚时,女人阴差阳错地与自己原来的心上人重逢。心上人劝她取消婚礼,跟他一起生活。女人挣扎一番,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失望,她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,与不爱的未婚夫结为夫妇。在此之后,她便开始感冒、咳嗽、嗓音沙哑,几个月都不见好,反倒愈加严重。
感冒作为一个微小的隐喻,在这篇小说,指涉着关于自由、自我意识等问题,当自我得不到彰显,那么全世界都会与你作对。小说结尾,女人终于想通,为自己而活,做一条自由的鱼,她感冒的症状才有了好转的迹象。

两年前,西西有两部长篇首次引进大陆,分别是《哨鹿》与《我的乔治亚》。这两部作品是西西实验文本中的典型。《哨鹿》看图说故事,灵感来自于郎世宁等人的《木兰图》。《我的乔治亚》则用看娃娃屋说故事的方式,让人直接联想起卡尔维诺看纸牌说故事的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。这两部作品的背景,都发生在十八世纪,而西西刚刚完成的新长篇,同样将舞台背景安插在了那个年代。
区别许多香港作家传统、幽深的笔触,西西的文字质感非常与众不同,可以从华语作家群中一眼区别出来,带有明显的西西风格。而她游戏般的讲故事方式则让她与西方的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具有一定相似性。这一点在学界中已被留意到,称之为“顽童体”或“寓言写作”等,但大众对这一点却单一地理解为“童趣”,而忽视了其中更深刻的先锋性。
台湾作家、乐评人马世芳忆及他的阅读经验,搜集西西的书,着迷于她的文字,受惠于她开启的文学世界。他写道:“她写战争、死亡、贫穷、老病,也带着一副柔软的心肠,和一双洞烛人世、然而始终好奇的眼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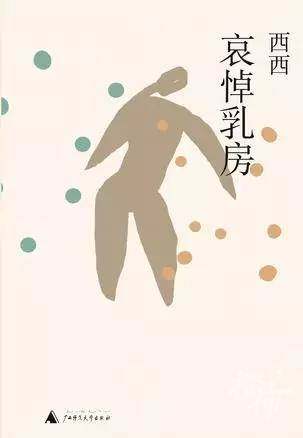
52岁时,西西因乳癌入院,并把自己治病的过程写成了《哀悼乳房》一书,手术后她的右手失灵,从此改用左手写作。
1996年,长篇小说《飞毡》出版,西西以轻盈的方式写下巨龙国的南方“肥土镇”——香港——一百多年间的种种变迁,从《我城》到《飞毡》,她的“肥土镇”书写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先河。
西西曾被纽曼华语文学奖誉为“华文世界最有童心的作家”。
她曾对记者说,27岁后,就停止长大了;她笔名“西西”,是因为“西”像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,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,“西西”意味着她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“跳房子”。
“手不离熊”的西西,手上抱的那只为“屈原熊”
她还用过很多可爱的笔名,比如麦快乐、叶蓁蓁、蓝尼罗河、小红花……业余时间里,西西喜欢画画、缝玩具熊、做玩具屋,在癌病后遗症导致右手失灵后,她曾以手制毛熊作为物理治疗,并写作《缝熊志》,描绘她手下“各有生命之独立熊”的背景掌故。

像孩子一样“玩熊”的西西——大概是当代香港女作家中,最特别的一位。
她的作品被陆续引进大陆出版,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她讲述自己亲手缝制神态各异、衣着萌美的布熊的《缝熊志》
,借由这本书,许多人爱上了这位可爱的香港老人。
“温情与善意,这是西西教我的。历史何其沉重,人生何其艰难,在世间行走,仍要怀抱温情与善意。不只对自己的族类,也要推及其他物种──因为这样,她写了《猿猴志》。”马世芳说。
《猿猴志》是西西《缝熊志》的延续,读下去,你才发现,其实看似童趣的主题,背后远为沉重。
她逼视灵长类的处境,“为人类发展上一直受歧视的生命说话”。那五十一尊西西手缝的猿猴,提醒我们“尊重生命”不该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。
“最有童心的作家”写衰老与生命时的笔触更是温润幽默。
今年出版的《白发阿娥及其他》收录了西西横跨20年写作的有关衰老的八个短篇故事,在《白发阿娥》一篇中,西西以七十岁的母亲为原型,写阿娥是曾经的玫瑰少女,如今微尘般的老人,她爱研究赛马经、给老家写信,她出门要抹风油精,到朋友家怕见人,在自己家和女儿与儿媳作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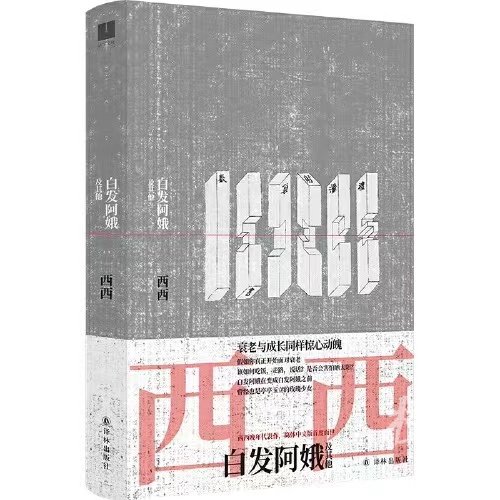
“白发阿娥可以做的事愈来愈少,使她发现自己愈来愈老。对于老的体会,她觉得生命不再前行,而是后退。比方说,当一个人活到七十岁,其实是退回到十七岁去……一直退一直退,最后回到O,势必成为一撮灰尘。”
如今,西西早已超过了母亲的年纪,变成了另一位阿娥,她迈着笨拙的步子,朝最纯粹的0走去,像来时一般。
如果这个时代仍需要文学偶像,西西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。
“我仍能散步,到大街上去看风景,看点儿书,写些字,精神饱满的日子,甚至可以去短途的旅行,既不愁一日之粮,又不用上班,还能苛求些什么?”
这位灰白头发的退休小学教师,眼瞳仍清澈如少女。这样一双眼,看遍了一座始终满载着躁郁焦虑的城,独身蜗居斗室,写出了舒展的天地岁月。
一路走好!西西!


